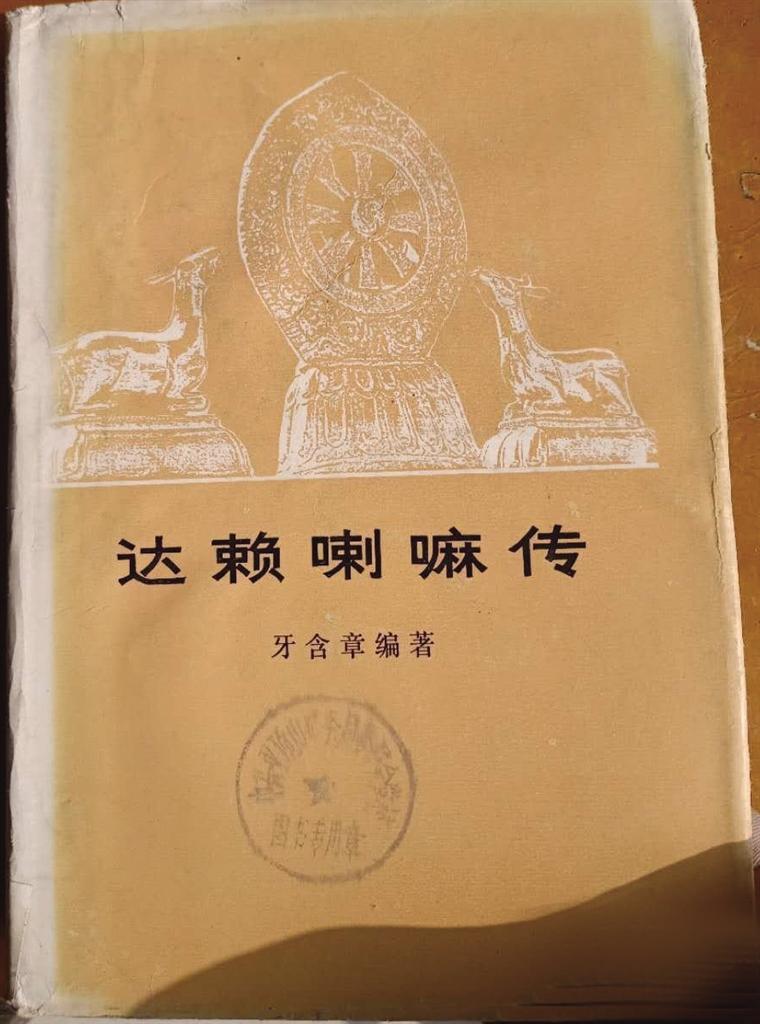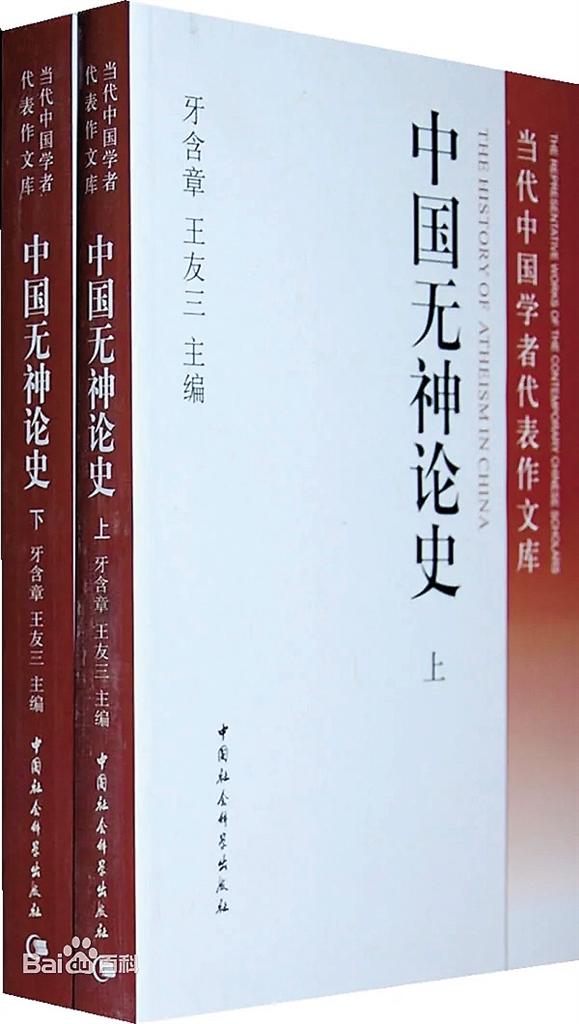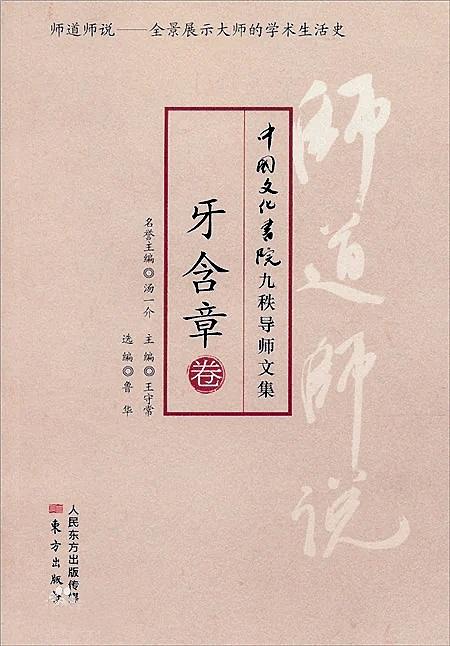◇包天锡
牙含章先生的一生是紧张繁忙的,也是曲折多彩的。
很多人都知道,牙含章先生是我们甘肃临夏州和政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藏学家。是他以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特殊的工作身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研考证,写出了《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和《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等重要专著,他还主编了我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和八卷本的《中国无神论史》等浩繁巨著。在西藏主权问题、汉族形成问题、民族的概念、回族的来历、宗教信仰自由的定义、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区别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原则问题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享受国家副省级待遇。
但一些人并不知道,牙含章13岁时父母双亡,同情者送他去夏河县拉卜楞寺穿起袈裟当起了小喇嘛,学习藏语藏文和佛经。三年后又有同情者带他到兰州国立第五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再无人供他上学,只好回临夏家里闲住两年。20岁时他又去夏河县拉卜楞寺,做了大活佛嘉木样呼图克图的汉文翻译和夏河保安司令部文书兼司令黄正清的秘书。不久,他又随嘉木样大活佛经青海到西藏,住进号称有喇嘛8800人的哲蚌寺,陪大活佛学经并任秘书和汉文翻译。这一路,他悉心观察了解,随时收集材料,整理出一本20万字的《青藏调查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热血青年牙含章得到大活佛同意并给路费支持,转道印度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到达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正当23岁的他整装待发奔赴华北敌后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闻天为书记、李维汉任秘书长的西北工作委员会,牙含章被分配到西工委的中央调查局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回回民族研究组。他以别名马尔沙,参与组织成立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会,并与负责回族文化促进会的杨静仁等回族同志相联系。1940年,24岁的牙含章和李维汉、刘春同志合作,完成《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他陪嘉木样大活佛进藏那次写成的《青藏调查记》书稿交给中央调查局,经第四分局局长贾拓夫审阅推荐,由延安解放出版社排出清样即将付印出版,却被胡宗南进攻瓦窑堡的敌军发现焚毁。1941年,年仅25岁的牙含章担任了第四分局少数民族研究室副主任及延安民族学院研究室副主任。
一些人更不一定了解,1946年3月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恢复至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这段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党指派牙含章和高健君两人到陇右地区开展党的地下斗争。牙含章化名康明德,作为少数民族工作部长和陇右人民游击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冒着随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和杀害的危险,在陇西、临洮、兰州、岷县等18个县市建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各民族中吸收了4000多名党员,游击队发展成2000多人,进行武装反霸,配合解放军解放陇右地区。1949年8月16日临洮解放,他担任中共临洮县委第一任书记,组织输送大批地下党员和知识青年支援新解放的地区工作。同年8月22日他的家乡临夏解放,之后不久,33岁的牙含章被任命为临夏第一任行政督察专员。他还成功争取黄正清,实现了夏河和平解放,黄正清后来曾任甘肃省副省长。1950年6月,他调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随后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委员、秘书长,护送班禅返藏行辕副代表。经过一年的紧张准备,于1951年12月19日出发,率领驻藏部队2000人,租用和调拨牦牛、骆驼、骡子和军马45000多头,驮运着生活和军需物资,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踏着冰雪封冻的长江黄河源头,翻越海拔5800米的唐古拉山。历时4个月,终于1952年4月28日安全护送班禅大师回到拉萨,当日实现了与达赖喇嘛时隔三十年的第一次会见。以后的五年,牙含章担任西藏工委委员兼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就是在这期间他写出《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初稿,直到1958年因患鼻癌经上海治愈后,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成立的民族研究所所长。
在民研所所长这个新职位上,牙含章先生顾不上自己是大病初愈应稍作休整,而是马上迎接一连三场极为艰苦而又严峻的大论战。首先是因为斯大林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又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了民族,而部族语言就变成了民族语言”。这两段话,被我国民族理论界一些人当作认定民族的基本原理,以至于因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1954年发表的《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秦汉时代的汉族已具备了形成民族的4个条件,立即引起我国民族理论界很大的震动,反对的文章一篇接一篇的发表了,它们认为范老的论点背离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因而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有了资本主义因素,汉族才形成为民族。而我国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够得上称为“民族”,全都是“部族”。由此引发的这一场论战,历时三年没有结论,范文澜先生坚持到底至死不渝。牙含章先生和支持他的同志们根据自己的研究认为,汉族的形成时间范文澜推断到秦汉时代这不是早了而是晚了。汉族形成为民族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商代以前,可能是在夏代。商代和周代的甲骨文及金文充分证明,那个时候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诸夏之族”,实际上就是汉族的祖先。到了汉朝才把“诸夏之族”改称“汉族”,汉族名称才算最后确定下来。牙含章先生同时认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早已经存在,只不过由于他们不同的经济生活,一般称之为“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商业民族”等等,把他们说成“部族”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新中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原则。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部落联盟是走向形成民族的第一步”,这些关于民族形成的基本原理的明确论述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了,而这场论战双方的文章中,都一个字没有提到。究竟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定义、民族概念和民族形成的问题,牙含章先生坚持实事求是和严谨科学的态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牙含章先生还主张“要大胆的敢于去碰国内外民族理论战线存在的各种问题”。还有两场论战,是以废除宗教特权、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为主的宗教改革问题和以废除农奴制度为主的西藏民主改革问题。1959年,西藏废除黑暗、野蛮和残酷的农奴制度,国内外有些人认为,民主改革不仅废除西藏地方政府的农奴占有制和西藏贵族的农奴占有制,同时也废除了西藏所有喇嘛寺庙的农奴占有制,这就是“消灭宗教”。为了从理论上阐明我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特约牙含章先生写一篇文章,他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十四期《论宗教信仰自由》的文章全面解释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信教或不信教是个人的自由,每个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还有,过去不信仰宗教,现在信仰宗教的自由,过去信仰宗教,现在不信仰宗教也有自由。既承认任何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又承认任何人都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是我们党的宗教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承认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就是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曲解”。他还强调,因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政府不能干涉。但是反动的宗教上层利用宗教特权,对劳动人民进行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这是不能允许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美国、日本等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刊物转载此文,认为牙含章这篇文章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统观念。事实上,在牙含章先生之前没有人这样全面、深刻的阐述过党的宗教政策,也没有谁把有神论、宗教和迷信三者加以清晰的划分区别。很多人误认为“宗教和迷信是一回事”,要保护一律保护,要消灭一律消灭。而牙含章先生主张加以区别,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取缔巫婆、神汉、相面、算命、看风水等骗取钱财的封建迷信。这为党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科学是无情的,论战是严肃的。论战求得了真理,论战也冲淡了人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一篇题为《牙含章和〈达赖喇嘛传〉》的文章,其中一句响亮的话告诉世人,“历史证明牙含章当年参与那几场论战的观点几乎完全是正确的。”三中全会后让他重回民族研究所所长职位,他又遵照党的要求赶时间完成《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两书书稿的最后一次修订,在1953年已写成初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近十万字新搜集的材料,让这两书早日出版。这两本书还被翻译成藏文和英文向国内外发行。他还建议科学院领导编著《中国无神论史》,他被推选为主编。他组织领导全国各有关机构的众多同志们共同努力编写近十年,终于1989年8月完成《中国无神论史》八卷本定稿,刚刚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到4个月,牙含章先生终因心力耗尽,于1989年12月19日凌晨在北京家中突然去世,享年73岁。
牙含章先生如此紧张繁忙的一生,哪有时间再多顾一件事情呢?刚刚完成牙含章先生生平事迹研究的甘肃省民委(宗教局)原副巡视员郭正清同志,现在竟又翻出牙含章先生多彩人生中鲜为人知的又一章。这就是早在1936年11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上连载发表了牙含章先生以笔名“冀达斋主”从拉卜楞投寄的花儿研究文章和他收集整理的一百多首花儿唱词,及关于花儿所涉地名注释的一封信。该刊编辑张亚雄先生指出:“冀达斋主自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字斟句酌,都经历了苦心抉择的功夫”。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一封来信,张亚雄编辑评价:“牙含章先生此段考证引经据典,皆以花儿为证,可谓渊博,如牙先生者,为编者帮忙不少”。牙含章先生花儿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他的长篇论文《花儿再序》中。这些作品,被张亚雄先生收编在《花儿集》一书中,于1940年在重庆出版。今天看来,牙含章先生不但是土生土长花儿故乡、真正精通花儿地道、对花儿进行学术研究的“开天辟地”第一人,而且他当年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依然是最高水准和正确方向。他搜集的花儿种类齐全、选择例证分析精准、对花儿规律探究精明、强调保护花儿的原生态。他当年发表该论文,才是20岁左右的年纪。如今,河州花儿已先后被列入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临夏州被确定为花儿的传承和创作基地,牙含章先生在天之灵应当十分欣慰。而郭正清同志遗憾自己长期在省上民族统战部门工作而且几乎是一辈子在研究花儿,却寻找当年的《甘肃民国日报》那份原件而终无所得,不得不托请牙含章先生的外甥女唐秀兰辗转千里电话寻访,才从牙含章夫人鲁华手上借到牙老保存的《花儿集》初版本。看到牙老在书上有三段批注和十多处用毛笔和红铅笔打的记号,但这时牙老已经去世,什么也采访不上了,只有深深遗憾。
本来有机会可以当面请教牙含章先生当年研究花儿的情况,这是1985年6月,郭正清同志正好在北京中央统战部学习,他和我及临夏军分区牛科长由我们州委宣传部唐振寰部长带领两次拜访了牙含章先生。他是个慈眉善眼很平和的人,还在家里用临夏的家乡饭“凉面”招待了我们。这样的气氛有什么采访不能进行呢?很可惜,当时郭正清同志对花儿的研究和对牙含章先生生平事迹的研究都还没有进行到这一步。17年后才想到,牙含章先生一生繁忙,他是什么时候收集和研究花儿的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研究者必须弄清楚。为此,郭正清同志急不可耐,穷追不舍,要我陪他采访牙含章先生的大妹牙伯琴老人。因为牙伯琴是我家十几年的亲戚,我还帮她写过回忆录,我知道她记性很好还善于认人,她曾认出换穿灰布解放军服对她家盯过哨的国民党特务。但在过去的谈话中,她从未提及她哥哥研究花儿一事。郭正清同志执意要去,想不到采访问题一提出,牙伯琴老人果然记得:“哥哥在兰州上中学时一回到家就关起房门写写画画,不让我们看。我虽然只上过小学,但我偷看了他抄写的那是山歌野曲。初中毕业回来两年还是整天写,大概就是你们说的花儿研究吧。”事情明白了,郭正清同志很快写成他的文稿,回来把这一段念给牙伯琴老人听,她说没错,我们这才放心了。牙伯琴比牙含章小4岁,牙伯琴和她丈夫刘敬儒都是牙含章先生亲自发展的地下党员,他们也为此经历了不少的惊险和磨难,幸好牙伯琴还活到了86岁。她的回忆,成为牙含章上世纪三十年代研究花儿的重要见证。